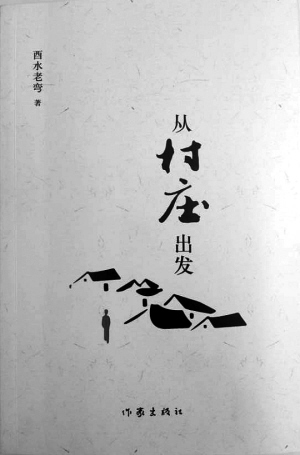
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曾因认真观察一枚苹果的落地,从而发现了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。世间万物,的确有一种潜在的力量,朝着一定的方向生长,不管其间的过程如何辗转,最后总要回归原点,使命完成的同时,便是另一个轮回的开始。
一座村庄,同样也有着自己的使命,就像《从村庄出发》的作者酉水老弯的“只有十来户人家的村庄曾家界”。他试图从曾家界出发,用个体的生命感召和体验,探寻这座村庄内蕴含的密码。他凭着自己的执着与命运的垂青,终究要带着独属于曾家界的胎记,跌跌撞撞地成长,曲曲折折地走向更远的远方。事实上,改革开放40年后的曾家界,这个地处武陵山深处、湘鄂交界处的土家族小山村,面貌早已今非昔比。
曾家界养育出的民族学教授酉水老弯,从村庄出发,先后辗转在湖北(恩施、武汉、荆州)、重庆等地,当岁月将他生命的血液调试得越来越稠浓时,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也随之渐趋发酵,直至血液里的每个细胞,蚯蚓一般蠕动着他的每一根末梢神经,直至淤积成这剂《从村庄出发》的解药。
事实上,乡愁自古以来一直就是文学作品中亘古不变的主题,只是从未像当下呈现出如此“井喷”之势。虽然当今多媒体和交通异常发达,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或稀释了血液里乡愁的浓度,但它潜藏在我们灵魂深处,令人魂牵梦萦。
对于从穷山僻壤的曾家界走出来的酉水老弯来说,似乎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越来越“走不出”曾家界。这种表面上的悖论,似乎更能反映出人性自身的矛盾:一方面千方百计逃离村庄;一方面却又时时念想着村庄。
在我的理解中,乡愁大致可以分为:纯粹式的乡愁,衣锦还乡式的乡愁,落叶归根式的乡愁。明显可以看出,酉水老弯的乡愁更接近第二种表现形式。
对于曾家界而言,酉水老弯就是村庄得意的作品之一。只是,这个土家汉子从村庄出发远行寻梦的旅途并非一帆风顺,兜兜转转30年的他,发现村庄的哲学在城市中似乎有些难以运用,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磕磕绊绊。总是走山路弯弯的山里人,却往往是直来直去的直性子。于是,换了一个又一个单位的酉水老弯,最终选择通过继续读书求学,并进入高校,还去英国做过访问学者,成为一名专做学问的博士、教授。
无论酉水老弯的工作单位抑或身份如何改变,都难以改变他乡愁的走向。一如那枚即将熟透的苹果,即便无人采撷,最终也会因为地球的向心力而“瓜熟蒂落”,直至最后与大地和村庄融为一体。
《从村庄出发》这部散文集,有非虚构的文本,有社会学的探究,更有深层次的情感渲染,完全就是作者自身形象的一个翻版。该书重点写了母亲、婆婆、爷爷,以及村庄的变迁,还有自己的求学经历和酉水河畔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。这些大量信手拈来的细节铺陈,让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成长史,解密出一个村庄的变迁和历史的嬗变,并引起同时代人的共鸣。由此,我们何尝不能将《从村庄出发》看作改革开放40年来,一个土家山村的编年史呢?
纵观全书,作者酉水老弯始终以第一人称的写作手法娓娓道来,如叙家常,且运用了大量的本土方言,使得湘鄂西的本土人士阅读起来更接地气,更具亲和力,更有家乡味。当然,任何事情都具有此消彼长的二元性。过多的方言使用,也容易导致非本土读者阅读的障碍,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文本的文学性。
《从村庄出发》的最大优点,我觉得有两点。其一,不动声色的叙述,使得感情节制而不泛滥,给读者较大的空间去感受、去体会;其二,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知识背景,来分析、来看待村庄的历史变迁,理性而丰满,具有一定的史料研究价值。另外,作品虽拘泥于日常生活的琐碎,却具有一股内蕴推动着文本前行,使得文本具有一定程度的可读性。这种内蕴,我们可以透过文本,理解为作者大山一般执拗的性格,以及一种永远不向命运低头的坚韧个性,从而使得自传体的《从村庄出发》更为真实可信,更具感染力。
一枚苹果最美好的归宿,不是跌落枝头,融进泥土,而是让这块土地的主人在丰收季节里,满怀秋收的喜悦,唱着幸福的歌谣,然后将她们轻轻摘下放进篮筐,再将她们一个一个“嫁”出去,品尝到属于她们专属的甜蜜。这才是苹果们最完美的归宿。就像乡村人之于村庄,如果一辈子被泥土攥住,从未走出过村庄半步,他的人生注定是不完美的。没有离开,何谈归来?更遑论故土与村庄的牵绊?
地地道道土家农民的儿子酉水老弯,毫无疑问也是他所属时代的幸运儿。村庄养育他的同时,将他送出了村庄,使得他与村庄之间拥有了空间意义上的距离,因此他才有了这本《从村庄出发》的另类村志。
当然,如果我们要求更为严苛一点的话,就像贾平凹之于商州、莫言之于高密,抑或当下非虚构范本梁鸿的《梁庄记》等等来要求酉水老弯,是有着一定距离的。我想,如果酉水老弯再进一步沉入村庄,运用他的专业知识,扬长避短,从学理的角度继续探究到底,或许会写出一个不一样的“曾家界”。
(责编 刘娴)
制作:李泓
订阅下载:2026年《中国民族》杂志订阅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