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近日,笔者(陈峻俊)对德国知名汉学家、特里尔大学教授卜松山(Karl-Heinz Pohl)就中西跨文化对话、中国文化传播、西方汉学教育等方面进行了线上访谈,择要刊发。
陈峻俊:卜教授好,我知道您非常热爱中国文化,能不能谈谈您是如何开始郑板桥的研究,或者您的汉学研究?
卜松山:我对郑板桥的研究始于1975年。1970年我开始在汉堡学习汉学,1975年我去中国台湾一年,以提高我的语言能力。在学习期间,我主要着迷于中国诗歌,但也着迷于绘画和书法,我在汉堡时已经开始用笔墨练习,我因此还辅修了艺术史。当时在中国台湾,我正在为我的硕士论文寻找材料。这时一位中国朋友推荐我读郑板桥的词曲。我开始研究和翻译它,于是就有了他的这组"道情"歌曲(指郑燮所作《道情十首》)的德文版。
我写信给我的德国教授——一位叫刘茂才的中国优秀儒家教育家,我非常敬佩他,我在信中问他是否可以将此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,他告诉我可以,但也说郑板桥还被称为画家(竹子和兰花)和书法家。所以我开始研究所有这些艺术传统,这也是中国美学最重要的一部分。
我还了解到郑板桥是一个十分迷人的人:一个非常关心普通人的“公务员”,但作为一个艺术家也是一个怪人——“扬州八怪”之一。在中国台湾学习访问后,我没有回汉堡,而是和当时的加拿大女友(很快成为我的妻子)搬到加拿大,在多伦多大学继续我的汉学研究,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。我在那里的教授Wayne Schlepp非常乐意指导我的课题,因此我后来写了论文《郑板桥:诗人、画家和书法家》,并在1982年完成了我的研究。然而,这篇论文直到近十年后的1991年才作为书籍(英文)出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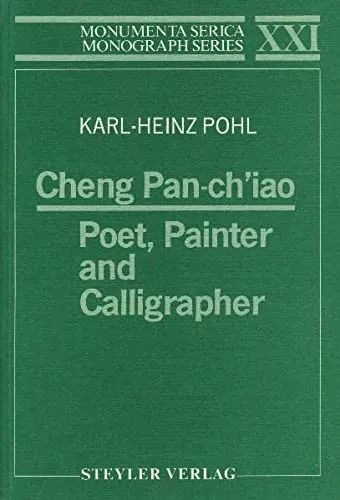
▲《郑板桥:诗人、画家和书法家》英文版 卜松山著。
陈峻俊:郑板桥给您带来了哪些影响?您在汉学方面的研究贡献是否从这里开始?
卜松山:郑板桥的研究对我有很大影响。首先,让我对一位著名文学家的思想和行动有了初步的了解。通过这些,我不仅了解了艺术(诗歌、绘画和书法),而且了解了儒家和道家在这些文学家的思想中是如何形成统一的。此外,我发现郑板桥对老百姓的承诺非常值得称赞,包括他在《郑板桥家书》中的儒家教育思想,顺便说一下,林语堂很早就将其翻译成了英文。
然后在2012年,我在比利时根特大学的博士生Mieke Matthyssen写了一篇关于郑板桥的重要论文:《难得糊涂和“糊涂的艺术”》。在书中,她展示了即使在今天,郑板桥的这句名言仍然非常流行,甚至成为一种社会运动,关于糊涂学也有很多相关的文献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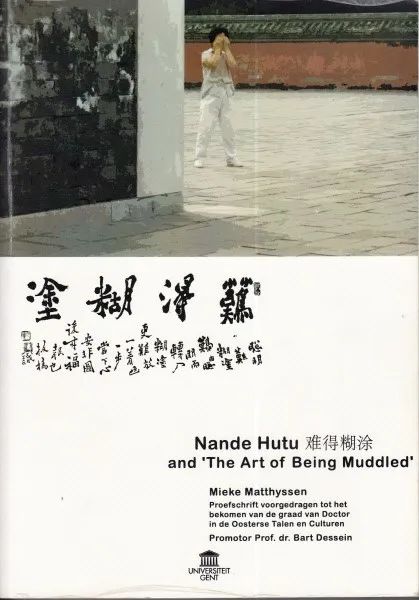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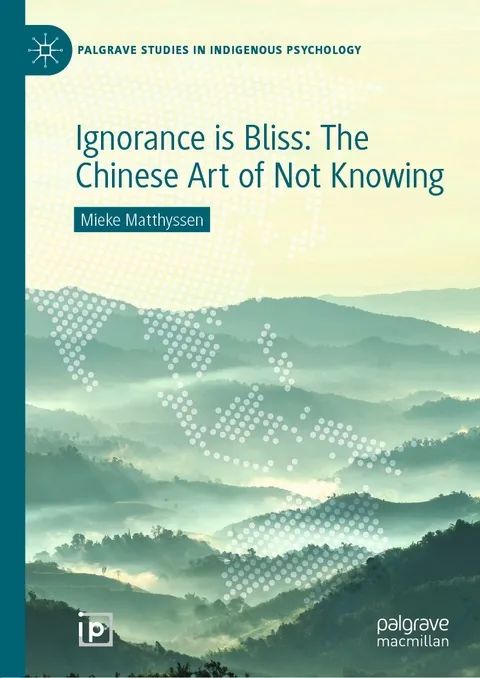
▲卜松山学生Mieke Matthyssen的书。
陈峻俊:您是《桃花源——陶渊明诗集》、李泽厚《美的历程》等书的德文译者,您认为中西方美学有何异同?
卜松山:是的,我把陶渊明的诗集翻译成德语。这是我在关于郑板桥的论文之后的第一个重要项目(1985年)。我对他的崇敬超过任何其他中国诗人;在这方面,我也许像苏东坡一样,也把他尊为最伟大的人。只是,不幸的是,我无法像苏东坡一样,为陶渊明的每一首诗写一首《和陶诗》……陶渊明的诗歌如此美妙,因为它们看起来如此简洁又生动。此外,它们清楚地揭示了背后的人和他的性格:“诗如其人”。当然,杜甫和李白也可以这么说。但是,陶渊明比他们要早几个世纪,而且在简洁中更显精彩。1991年我在北京第一次见到李泽厚时,我问他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是谁,他回答:陶渊明。我很高兴我们在那时就找到了这种共同点。
现在说说中国的美学。西方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。在西方,它不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。而在中国历史上,美学可以说被认为是探究艺术和文学创造力的一种特殊的“中国方式”:即诗歌、书法和绘画的本质。中国美学还与文化认同有密切关系。大约150年前西方思想传入中国时,中国人认为中国文化是由美学塑造的,而西方文化是由基督教塑造的。蔡元培就主张:“以美育代宗教”。在我看来,中西两种美学之间的差异比相似之处更重要——而且也更有趣。中国美学主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,更多的是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。和谐、阴阳平衡、对形式的认识(平仄、对仗)、自然的创造力和活力(气韵生动)发挥了作用。
例如,在绘画中,人们所追求的不是对自然的真实描绘,而是对精神和思想的传达。此外,还有绘画、诗歌、书法的和谐,最后还有红色印章的和谐。在西方美学中,“美”起着重要作用;但在中国传统中,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。因此,我理解中国现代美学家试图在中国传统中寻找“美”的做法,而是一种跨文化——创造性的——误解。然而,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。

▲2015年在夏威夷与李泽厚。(卜松山 供图)
陈峻俊:郑板桥认为“趣在法外”,您怎么看待中西目前面临的对话现状及您的建议?
卜松山:我熟悉中国美学中使用"趣在法外"一词的提法。我非常重视它们,也总是试图把它们传达给西方观众,因为它们对理解中国美学至关重要;例如,“意在言外”“景外之景”“象外之象”,我们从司空图开始就知道关于诗的性质的表述,或清代黄钺的“妙在画外”。在我看来,中国美学的生命力来自于有规则和无规则或自然和法之间的张力,或来自于遵守规则同时又超越规则,这可以用“活法”一词来表达,或用石涛的名句“无法之法,乃为至法”表达。
现在谈谈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对话。当然,对话有很大的“趣”,这种“趣”不能用规则来把握,特别是如果它是中国和西方之间的“对话”。此外,这种对话也许更属于政治和媒体领域,而这些领域有自己的“法”。由于政治原因,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理解现在已经变得非常麻烦。人们把这个结果比作聋人的对话。
每一方都只谈自己的优先事项,因此不了解另一方。但就富有成效的对话的先决条件而言,这包括对对方的充分了解,例如通过关键经文的翻译。在这方面,中国和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对称性。因为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,几乎习得所有关于西方的知识——从哲学到文学、艺术、社会科学以及更多。相反,普通的西方人,包括知识分子,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,既不了解其传统,也不了解其现状。如果能消除这种基本的不平等,也就有可能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。我正在努力,在我有限的框架内,帮助我的国家的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。也许这已经是对对话的一个小小的贡献。
陈峻俊:我知道您还担任德国特里尔孔子学院的院长,您在推广海外汉学教育方面都有哪些心得?
卜松山:过去德国的汉学有一个发展趋势,就是基本上只关注现代中国。这样,学生对语言系统的掌握就得到了重视。这样做自然没有什么不对,但却因此留下一些空白。如果一代代汉学学生成长起来了,他们对具有几千年丰富文化历史的过去却知之甚少,这不是非常令人遗憾吗?因而我希望,汉学专业的设置,也要重视中国的过去,这是理解现代中国的基础。对大部分学生而言,他们对古汉语不太感兴趣。我试图告诉他们,如果要阅读比较高深的文章,总是会碰到一些古代的典故及名人引语等等,即使只读报纸,也绝对离不开古代汉语。
试想一下,一个日耳曼语言学者,他只了解现代德国,从没听说过歌德、席勒,更不知道康德、黑格尔是何许人也,那我们可能会说,他对德国的知识面太过狭窄,应该增加对历史的了解,因为只有了解历史,才能更好地了解现代。中国拥有最源远流长、从未间断的文化史,是传统文化的巨大财富。人们不应忽视古代中国。而且,古代与现代之间存在何种联系,这是个有趣的问题。所以我认为一个完整的汉学专业必须这两方面都要兼顾。我当时这样做,也很受学生欢迎。
受访者简介:

卜松山(Karl-Heinz Pohl),德国知名汉学家,特里尔大学教授,1945年出生于德国萨尔路易,曾任德国图宾根大学中国文学与哲学教授,特里尔大学文学与媒体学院前院长。卜先生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思想史、伦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美学以及中西跨文化传播与对话等。著有《全球化语境里的中国思想》《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》《发现中国:传统与现代》(即将出中文版)、《中国美学与文学理论》《儒家精神与世界伦理》等学术专著专论;德文译著有《美的历程》(李泽厚)、《陶渊明全集》《桃花源——陶渊明诗集》等;近年多次应邀赴中国讲学,为清华大学、武汉大学客座教授。
作者简介:
陈峻俊,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。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副会长;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理事、民族影视专委会秘书长;湖北省新闻传播教育学会副会长。湖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。
来源:“道中华”微信公众号
作者:陈峻俊
编辑:刘雅
流程·制作:韩东峻
订阅下载:2026年《中国民族》杂志订阅单